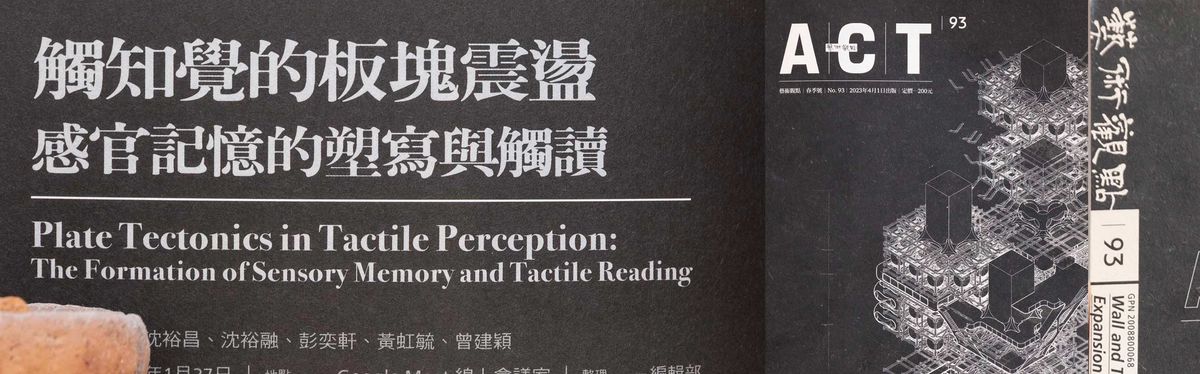
藝術觀點 春季號 No.93
「長城與巴別塔:當代媒介的管制與擴延」
土星工作室很榮幸接受沈裕昌助理教授、沈裕融助理教授邀請參與本期藝術觀點專題當中的「陶瓷圓桌討論會議」,由土星工作室主理人 黃虹毓、彭奕軒、藝術家曾建穎,聊聊對土的感受性,藉由動態的觀察以及這幾年參與、協辦過的展覽「壞坏」、「水土不服」,進行一場非常有趣的對話~


觸知覺的板塊震盪 感官記憶的塑寫與觸讀
Plate Tectonics in Tactile Perception:
The Formation of Sensory Memory and Tactile Reading
本文節錄於藝術觀點 P.32-36之文章段落
彭奕軒(以下簡稱彭)——
回到「土」的媒介性思考。我觀察到虹毓的作品,近期十分關注與「環境」的關係。「土星」曾經做過許多與「原土」相關的計畫,藉由原土採集的各種過程來認識「土」。通常,我們購買一包進口土,直接開始使用、捏塑,可能鮮少思考土的來源與外在環境的關係。我想起兩年前,台灣曾經有過一次大旱,在一個新聞報導中,一位水庫管理 局的工作人員說:「你不要看現在下了一場雨,就以為可以解決乾旱的問題。」乾旱的問題並沒有被解決,因為「大地應力」(tectonic stress)的關係——意思是說,土確實接受了一些水分,但它的作用力,卻是非常緩慢的。當然,「大地應力」的概念,指得是「板塊移動」,它非常緩慢地進行,是幾乎無法用肉眼察覺的時間感與動態感。
而虹毓最常運用的「絞胎」手法,就是不同土種互相疊合、拍打、擠壓的結果。因為不同土之間,其實都有不同的「應性」或是「應力」,不管是在濕軟、乾燥,或是在素燒、釉燒的階段,它其實都在運動。當我們把這些細微的東西放大來談,最有趣的點在於,「土」跟「土」之間,其實有著「接納性」與 「排他性」,它同時存在著這兩種狀態。我們近期剛完成一件故宮南院的裝置〈土間〉,那個計畫其實就是做出一塊一塊的「土磚」。當時,虹毓講述了一個非常迷人的畫面。我問:「妳為什麼要在硼板上要放砂,然後去燒製?」她說:「放砂的用意在於,陶瓷在燒製的時候其實會移動,若不放砂,移動的過程可能造成土的破裂。砂的作用就像輪子,讓土可以慢慢地移動到它要移 動到的地方,而不會被撕裂。」正因為這個畫面是不可見且難以被覺察的,所以當它被講述出來的時候,便特別地迷人。
融——奕軒剛才一直提到一個關鍵概念,就是「土的運動」。面對「材料」的時候,我們很容易把它視為一個「靜止的物」。可是「土」卻告訴我們, 事實上並非如此。「土」是一個「動態的物」,它沒有靜止的時候。水氣、乾燥、燒製,都會造成狀態 上的改變。這裡所說的「運動」,不只是剛才談到燒製過程中的位移,同時也包含各種物理狀態的持續變動。這些變動十分緩慢,卻未曾間斷,很多變化甚至是在不可見的狀況下持續發生的。從「製成」到「乾燥」,「素燒」所產生的「收縮」,「出窯」 時持續發出「吭啷吭啷」的細微聲響,這些都是最好的證明。

沈裕昌(以下簡稱昌)——我想先回應一下剛才談到的幾個點。虹毓提到「轆轤」時,讓我開始思考, 為什麼妳會覺得需要「停下來」?因為「轆轤」可以說是最早讓人感受到「抽象速度」的工具發明。
麥克魯漢(Marshall McLuhan, 1911-1980) 在分析「輪子」的時候,曾經簡短地勾勒出從「轆轤」、「車輪」到「電影播映膠卷」的發展歷史。這三種「輪子」,在不同的面向上,都擴展了我們過去所能觸及的疆域,並放大了我們的感官和思維。 交通工具上的「輪子」並不限於「車輪」,「方向盤」也是「輪子」。操縱汽車「方向盤」的經驗,與使用「轆轤」的經驗十分相似,也即一個非常微小的動作,會被放大成一個劇烈而無法控制的後果。
「加速」同時也意味著「放大」。當我們使用我們的「手」去觸碰東西的時候,很多時候並沒有意識到,從指尖、指腹、指節到掌心,存在著各種方向與程度的施力點。在轆轤上,你所有的「觸碰」都會被放大,甚至因此造成失控的狀態。所以在「拉坏」時,一開始要「定中心」。「中心」當然不是一 開始就「定」在那裡的,而是需要你把它「找」出 來。中心未定之前,在轆轤上因為高速旋轉而劇烈扭動著的土塊,讓人想起駕駛汽車時因為任意扯動方向盤造成車體左右擺盪的狀態。因此,面對失控時的暫停,我覺得很像是一種驚嚇反應。
虹毓提到「土」的時候,討論到「生命」,我覺得這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隱喻。這其實是通過「轆轤」去思考,對於一個有限性的存在而言,面對超出人能理解的巨大事物(比如說「生命」、「關係」),究竟能採取何種有效的應對方式?這是操作轆轤時, 非常有趣的思考經驗。另外,妳剛才也提到,妳對處理泥條的過程十分著迷。我覺得,「泥條」跟人類的「手」之間的關係,是非常純粹的。因為我們的「手」長有「對生拇指」(opposable thumb),而「對生拇指」從演化的功能而言,原本是為了抓取 「樹枝」。在搓製「泥條」的過程中,人會一直不斷地意識到,手的指掌平面,其實並不那麼平整。我覺得「泥條」的發明,或許來自人的「手」對於「樹枝」或「棍狀物」的「器官記憶」。因此,「泥條」疊加的過程,也可以被想像為「手」對於「棍狀物」 的「記憶」之「重疊」。


也就是說,「泥條盤築」可以被理解為「觸覺記憶的重疊」,正如同「電影」可以被理解為「視覺記憶的重疊」,兩者的感官經驗是十分相似的。我記得有一位做陶瓷鑑定的朋友告訴我,當他們在鑑定這種特別是轆轤製作的器皿時,通常所使用的方法, 是用拇指與食指的指尖,同時且對向地捏著容器的內側與外側,然後閉上眼睛,從「圈足」往「口緣」 的方向,垂直地向上摸。在摸過幾次之後,他就可以透過他的「指尖記憶」,去進行器皿的鑑定。也就是說,透過轆轤塑造的土,每一圈都是對於指掌動作的鉅細靡遺的記憶。這個記憶的時間方向,是不斷向上的,與我們在看影片時,視窗底下的時間進度軸,是一樣的意思。在此一操作中,「土」就 像「膠卷」一樣,把整個行動的過程記錄下來。但是「土」特別的地方在於,你必須藉由「觸覺」,才 能更清楚地閱讀這份紀錄。因此,我們的「手」, 就像「讀寫頭」,它既是資訊的「輸入端」,同時也是「輸出端」。只有通過「手」才能夠「輸入」這些 資訊,同時「輸出」以讓我們重新「閱讀」這份紀錄。換句話說,「手」就像且同時是「陶」的「錄製器」與「播放器」。當鑑賞者把玩這個土器,或是創作者把玩自己做的土器,其實你摸的並不是土,而是過去的你所留下的手的痕跡。這就產生了某種 「跨越時間的手談」。
另外,奕軒過去曾經向我提及,「人走在土地上」,或許可以被視為最早的「製陶」。這個思考似乎指向了「文字的起源」,比如許慎在《說文解字序》指出,倉頡是「見鳥獸蹄迒之跡」才「初造書契」。而「鳥獸蹄迒之跡」,必然是留在「土」上的 。「 土地上的足跡 」, 回應了前面提到的 ,「 土 」的其中一項特質,就是能夠快速地留下行動的紀錄。這些紀錄,儘管就視覺而言是可見的,但卻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。因此,面對這些紀錄,只使用視覺是不夠的,還必須通過觸覺的理解,才能把握其豐富意涵。這些「泥土上的痕跡」,具有一種非常獨特的,介於「手」與「眼」之間的矛盾辯證關係。如果我們以古希臘雕刻的目光來觀看像「維倫多夫的維納斯」(Venus of Willendorf)這類的雕刻作品,確實很容易認為它「比例失衡」,並將其原因歸咎於「誇大表現」。可是我們應該要注意到,它的尺寸只有11.1公分,因此它的鑑賞方式,其實更接近於土器,而不是古希臘雕刻。它應該要像土器一樣被你包握在手裡面把玩,而不是隔著一大段無法觸及的距離去觀看。如果你把玩它,而不是遙望它,那麼從視覺的角度來看認為它誇大的地方, 從觸覺的角度來說就並不誇大。因為通過觸覺,唯有這樣的造形才能夠被快速地辨識,同時喚起相關 的觸覺記憶。土器,和維倫多夫的維納斯一樣,必須通過「把玩」來理解。唯有通過「手」,作為「觸覺記憶」的讀寫頭,才能夠幫助我們閱讀「另一隻手」所留下的抽象痕跡。
全文請至全台各大通路購買《藝術觀點ACT ——春季號 No.93》
購買、通路連結:https://reurl.cc/d7Ydk2
